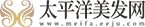2021年,媒体人、摄影师蒋理以“敦煌文化守望者”身份,在敦煌学习、生活了四十天。在这四十天里,他与其他守望者一起,展开了作为敦煌讲解员的“修炼”,讲述敦煌的历史地理、莫高窟的开窟概况、各个时期的经典洞窟、敦煌守护者们以及莫高精神,揭开众多不开放洞窟的神秘面纱,窥见窟顶治沙、洞窟数字化、壁画修复等敦煌绝技,见识了一个璀璨、多元、神秘,但又与每一个人都能够产生关联的并不高冷的敦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这份“修炼”结束的时候,蒋理将其经历、见闻和感受整理为一本书《敦煌守望四十天》,书中200幅彩图,亦是眼到心到神游敦煌的纸上之旅。经出版方授权,第一财经摘取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第十六天 | 五代61窟:五台佛光
今天进入莫高窟较早,窟区目力所及之处,空无一人,有种全窟包场的霸气感。但可惜17窟的考核开始之后,就变成霸气侧漏了。
今天遭遇了讲解培训以来的第一次“短路”。17窟非常小,游客们不能进入其中,同时此窟又是每一个游客必到之处,团队很多,因此正式讲解只能在远离洞窟的地方盲讲,没有任何洞窟图像可供参考。再加上今天有纪录片团队跟拍守望者学习生活,我在讲解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莫名的紧张。
而当我意识到自己紧张的时候,这种紧张就瞬间嚣张了数倍,彻底把头脑里面的洞窟内容全部挤了出去,导致大脑出现“黑屏”。由于现场没有任何图像可做提示,我估计自己至少黑屏了20多秒,对着空气尬笑了数次,忝称“连词第一”的我,终于也第一次出现了“无词可连”。最后我强制重启了大脑,把后半段内容还算顺利地讲完了。17窟真像是一个“黑洞”,今天不只是我在这里“短路”,另外两位平时解说流利的小伙伴,也纷纷在这里“翻船”,我高度怀疑我们在那一刻被王道士附体了。
另外,这一窟还出现了几个极易“跑偏”的词语。比如洪辩法师被封为“河西都僧统”,一旦记成了“河西都统僧”,就很难纠正过来;比如来到藏经洞的探险者“吉川小一郎”,如果念成了“小川吉一郎”,即刻就会在大脑当中生根。为了能够“去伪存真”,大家都像学习相声贯口一样练习起来。于是,洞窟考核结束之后,依然能听见藏经洞陈列馆院落中,回荡着绵延不绝的“河西都僧统”“河西都僧统”“河西都僧统”的奇异呼唤声。
曹氏归义军
从17窟通往 61窟的路挺长,一路听着刘老师的讲述,就感觉自己正从晚唐慢慢走向五代。对于大唐来说,这是一个四方割据、波诡云谲的没落时代;而对于敦煌来说,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特殊时期。
在公元848年,敦煌英雄张议潮率军起义,赶走了吐蕃人,被唐王朝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成为了河西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张议潮及其子孙统治敦煌的时期,就被称为“张氏归义军”时期。当历史推进到晚唐五代之交的时候,此时的“归义军”已经没有了张议潮手握河西十一州的盛况,管辖的主要区域收缩为瓜、沙二州,而手握权柄的是张议潮的孙子张承奉。他试图重现祖父往日的荣光,同时与东西方向的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政权开战,但却被两面夹击,损失惨重。最终在后梁乾化元年,也就是公元911年,张承奉被迫与甘州回鹘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张承奉病逝之后,沙州豪门大族公推曹议金为节度使,拉开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大幕。而我们现在走进的61窟,就是由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议金之子曹元忠所开凿修建的。由于窟主不同凡响的身份和地位,61窟也具有了远超他窟的宏大气势。
从《五台山图》到佛光寺
这个洞窟当中最震撼人心的是西壁通壁所绘制的《五台山图》,这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总面积达46平方米。整个壁画极为精彩:上部云移风动,绘制了各种天人飞临五台,赴文殊菩萨法会;中部描绘了五台山五峰擎天,寺院云集,各种灵异画面,穿插峰峦之间;下部则展现出从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县)经五台山到山西太原之路,以及沿途的风土人情。
我们仔细观察着这幅壁画,就像多年以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书中初见这幅壁画时一样。这对著名的建筑学家夫妇在法国人伯希和编写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见到了这幅《五台山图》,他们仔细端详,思索良久,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图像当中描绘出的一座寺庙上,那就是——“大佛光之寺”。
1937年,在战争阴云笼罩之下,梁思成和林徽因踏上了前往五台山的道路,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区域发现了佛光寺东大殿。这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唐代殿堂式木构建筑,被梁思成誉为古建筑当中的“第一国宝”。它的发现打破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建筑的谬论,也给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看着窟壁上的大佛光寺,我不禁想到了我生活中的另一座寺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1934年也来过我居住的甪直古镇,他们特意到此考察镇上的保圣寺大殿。这座江南地区屈指可数的北宋木构大殿,就没有佛光寺东大殿那么幸运了。在梁林夫妇来到甪直之前,它被作为一件残损的生活用品,而不是珍贵的艺术作品,毫不留情地彻底拆除了。
《五台山图》深深打动我的地方,还在于它留下了1 000多年前的平凡生活场景。图画之中有农夫正在推磨铡草,有山人正在砍柴负薪;有店家正在屈膝迎客,有伙计正用杠子压面;有商人正在拉驴前行,有驼队正在翻山越岭;有香客正在献上供品,有信徒正在塔下跪拜;有老友路中偶遇,有新客山间问路;有人山中遇雨,有人城内小憩……
每一次在壁画之中看到这样没有名姓的小人物,我都觉得亲近。他们像极了我和身边熟识的那些平凡朋友,每一个人都在认真地生活,享受人世的欢乐,也承受凡间的苦痛,创造着人间的鲜活百态。在只有满天神佛的地方,如果看不到自己,那于我和我的生活而言,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华衣之下的外交婚姻
不仅仅是巨幅的《五台山图》,61窟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加大号”的,也包括供养人像。所谓供养人,就是出钱修窟供奉佛祖菩萨的人,他们的画像有资格被留在窟壁上。在之前我们看过的很多洞窟当中,供养人像都画得很小,位于洞窟最下部,常常漫漶不清。但在61窟中,由于供养人地位显赫,画像极大,几乎与真人等高,尤其是女供养人像,衣饰华美,妆容典雅,让人见之忘俗。刘老师告诉我们,这一窟的供养人像不仅仅是研究古代服饰妆容的绝好素材,还反映出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真实的生存环境和成熟的外交手段。
如果回到五代时期,我们将会看到:敦煌城内张灯结彩,喜气冲天,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曹议金正在迎娶甘州回鹘可汗之女天公主,归义军与东面的甘州回鹘正式联姻。我们还会看到:敦煌城门大开,送亲使团绵延数里,这是曹议金将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于阗国王李圣天,归义军与西面的于阗国也结成秦晋之好。多年之后,曹议金又将他与天公主所生的一个女儿嫁给另一任甘州回鹘可汗,实现了亲上加亲。曹氏归义军正是充分利用了联姻这一手段,为自己的统治争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生存空间。
这些联姻中的关键人物也出现在了61窟的供养人像中。洞窟东壁南侧的壁画上,排在首位的供养人像身着回鹘装,她正是曹议金的回鹘夫人天公主;第二位供养人也着回鹘装,她正是曹议金和回鹘夫人的长女,嫁给另一任甘州回鹘可汗为妻;第三位供养人着于阗装,她正是曹议金的另外一个女儿,嫁给了于阗国王李圣天;而排在第四位的供养人则是曹议金的原配夫人广平宋氏。按照我们熟知的传统礼仪,广平宋氏应该排位靠前,因为她既是曹议金的原配夫人,又是窟主曹元忠的生母。但事实上,她只是排在了第四位,甚至站在了两位女儿辈的妇人之后。很显然,这是亲情让位于政治了。
于阗王后
在这几身供养人像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站在第三位的于阗王后。她头戴凤形金冠,鬓插华丽步摇,身穿大袖襦裙,颈戴绿玉项链,脸贴美妙花钿,仿佛随时都会从墙壁上走下来。
看到她脸上时尚的花钿,我想起一个南朝故事。那是一年的正月初七,含章殿前梅花树下,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正在卧榻之上仰面小憩。清风拂过,梅花飘飞,正好落在了公主脸上,留下了一个花瓣状的印记,而且久洗不掉。宫女们看见之后觉得很美,于是争相效仿,将梅花贴在自己脸上,流行一时的“梅花妆”就此诞生。
我仔细端详着这位远嫁于阗的曹家女儿,试图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一些心情。但她似乎面无表情,不喜不悲。这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异国宫廷而修炼出来的“保护色”吧。作为一场政治婚姻的女一号,她远嫁异族,身入西域,放弃了儿女情长,肩负起家国安危,在无人护佑的地方,她必须隐藏起真正的喜怒哀乐,因为任何一点松懈,带来的都有可能是身死国危。
我无法猜测这位曹家女儿获悉自己命运之后是何心情,她嫁入于阗国之后又是否有过孤单无助。但从敦煌遗书中的记载来看,她如同文成公主一样,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对两个政权关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她的亲生儿子后来也继位成为于阗国王,为双方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但比文成公主幸运得多的是,这位于阗王后在暮年又回到了阔别许久的家乡敦煌。只是不知道当她像我一样站立在这幅供养人画像之前,看见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故人故事心上过,眼中是否依然还能如此无喜无悲。
“十二星宫”
当我正在与这位于阗王后神交的时候,有同伴好奇地问:“这一窟为什么没有男供养人像呢?”刘老师回答说:“原本曹氏家族的男供养人像都绘制在洞窟甬道两侧的墙壁上。”但我们抬眼看去,那里只有满天的神佛。刘老师指着位于甬道壁上不起眼的边角处的一幅孤零零的画像解释道:“在元代或者西夏时期,那些高大的男供养人像,被这位洒扫尼姑雇人新画的壁画给盖住了。”
所谓洒扫尼姑,就是寺庙中负责清洁工作的尼姑。她供养的这幅壁画,正是莫高窟壁画中的孤品《炽盛光佛图》。我惊奇地看到,壁画中除了有可以“消灾避难”的炽盛光佛、九曜星神、二十八星宿之外,竟然还画出了十二星座:双子、处女、白羊、双鱼……刘老师告诉我们,这其实是源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
据说这套星宫体系自隋代传入中国之后,宋代时已经广为流行于民间。我的偶像苏东坡,也是一位超级星宫发烧友,虽然不知道他是否每天都要看看星宫运数之后才会出门,但他曾经在文章中写道:
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可见东坡不仅能够熟练推断别人的“星宫”,而且可以分辨是“太阳星宫”还是“月亮星宫”,进而还能根据所属“星宫”给人“算命”。这不,他就给大诗人韩愈和他自己算了一次:因为韩愈的“月亮星宫(身宫)”是摩蝎(羯),而东坡的“太阳星宫(命宫)”也是摩羯,所以两人“多得谤誉”,同病相怜。想到这里,我心生慨叹:当年东坡先生窘迫黄州,要是拿出“星宫占卜”这一压箱底技能,哪里用得着日晒雨淋春耕秋忙啊!
虽然十二星宫很让人惊喜,但我还是对那幅孤零零的洒扫尼姑像更为在意,画像中人物身形瘦弱、姿态虔诚。在某年某月某日,正是这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用尽她一生的积蓄,请画师为她在甬道上画上了这幅全新的《炽盛光佛图》。而与此同时,“曹氏归义军”那些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们,便被她和她唯一的壁画永远地遮盖了。
《敦煌守望四十天》
蒋理 著
中华书局 2022年7月
标签: 敦煌石窟